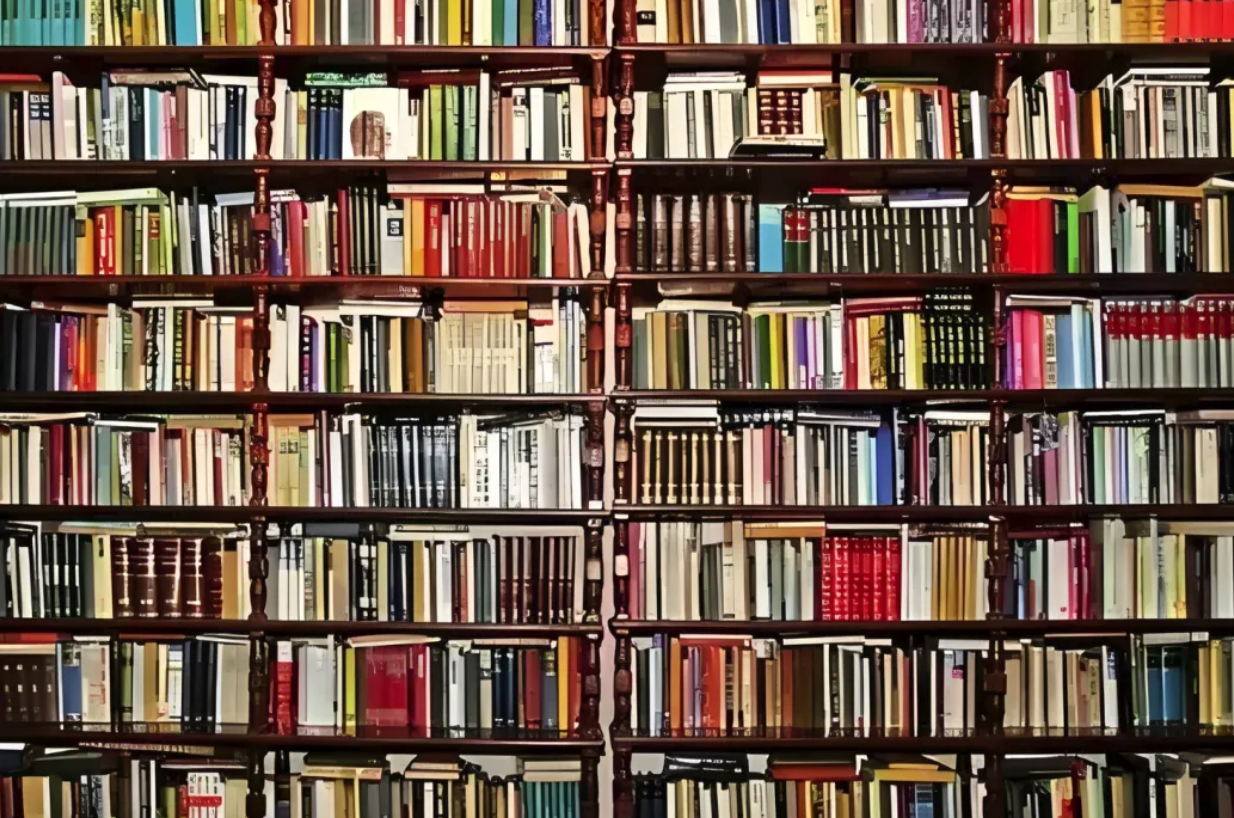
水与油:两种写作体温的七把钥匙
兼作《散文》《北京晚报》五色土
与《羊城晚报》花地文艺副刊
创作笔记
作者|邵文杰
缘起陶然亭西南隅的一次走神
秋日清晨的北京陶然亭,像一方半旧的青玉,被薄雾轻轻托在掌心。我沿柳枝低垂的弧线拐进西南隅,木椅微凉,漆色剥落处露出松木质地,如岁月亲手揭开的旧痂,又似古琴面板被指尖磨亮的温柔。湖面尚未醒来,晨光却已抵达,像谁遗落的一枚铜镜,被风反复擦亮,亮得近乎羞涩。镜心浮着昨夜画舫遗落的彩油,薄而轻,似一段不肯落地的绮梦,颜色在冷冽里仍带余温;镜缘深处,淤泥与时光交缠成深黛,如一泓被岁月熬浓的药汁,苦涩中自有安神的静香。
忽有鸟翅掠过,剪开一线水纹,也剪开了我的恍惚——文章原也分水、油两味。有的词句如油,光华璀璨,却只浮于眉睫,转瞬即干;有的字句如水,清寒透骨,却一寸寸渗进骨缝,替人收藏云影与回声,日后在暗夜里自行发光。
《散文》似水,《北京晚报》五色土如雨后京郊的壤土,带皇城根儿的潮腥与温热,《羊城晚报》花地则如油。仲夏朔日,花地以头条位置托出《宛丘听风》(2025年8月5日《羊城晚报》花地文艺副刊),当日便被新华网客户端推上首页,屏幕上的八十五万次心跳,替岭南湿热再添一度。一念既生,便想以经年新闻从业的光阴为烛,铸七把钥匙。若能为彼此各启一窗,窥见报刊背后鲜活而生机勃勃的文艺生态,便不负今日湖光的馈赠,让文化的热度有了湿度,像木棉落在掌心,数字便化成了体温,让文字澄明如镜。
以下七节,每节循一径:先说写作心法,出自日常书写之实在经验;再作三刊对读,辨析《散文》《五色土》《花地》编辑理念与审美偏好如何潜在地形塑文本;最后落回自我审视,以我已发表作品为例,回溯从灵光乍现到落笔成章,再到修订刊发的全过程。如此往复,既是一次向内整理,亦是一场向外对话。
钥匙一:平时功课让地理与呼吸先行
写作心法:散文写作,最忌提笔即写。眼之所见,未必是笔下该留。我一直相信,好文章在动笔前早已开始。它始于一次驻足、一阵风来、一抹来不及命名的气息。
我有习惯,每至一处,必做“气味地图”。不画于纸,而以心为笺,以呼吸为笔,录下此时此地之独特气象。如在淮阳龙湖,春日藕节挣破黑泥,带冷冽的腥甜,如婴儿初啼时含于舌尖的羊水;夏日荷叶翻背,露灰白叶脉,风过处散出淡腥的药味,似母亲旧年煎的荷叶茶;秋夜桂香沿水岸爬升,甜中藏苦,如母亲最后一次为我掖被角时指尖的温度;冬晨冰裂,“咚”一声自湖底传来,仿佛大地在胸腔换气。
我将这些封存于意念,贴上一枚时间邮票。写作中途若遇淤塞,便“拆”一封。往往气息重现瞬间,遮蔽的场景纷纷苏醒,词句自有归处。
刊物对读:《散文》自1980年创刊,便带素衣教书先生之气质——不喧哗,自有声;不张扬,却极深厚。其推崇之“淡”,是繁华落尽后的真淳,亦为苦心经营后的看似不经意。
《五色土》1958年随《北京晚报》诞生,其名取自社稷坛五色土,意喻“京华风物,尽收方寸”。如一条可漫步的胡同:书乡、文史、城迹、胡同、品读,五步一景,十步一轶。
《花地》1957年创刊于广州,天生带岭南湿热与木棉炽烈。它要热闹,要表现,要第一时间将生命热力泼洒至读者眼前。
地理于此,不再是风物标签,而近乎一种美学立场与文化精神底色。
自我审视:《天山的雪》刊于2025年第9期《散文》,写我援疆三载,积二十三种雪声:雪落松针如翻极薄经书;雪崩前一瞬如万匹野马扬蹄胸腔;雪水渗土如母亲为远行孩子掖被角;雪融夕照如极夜亮起的酥油灯……这些声音写于桦树皮,卷成小卷塞入牛皮囊悬于床头。夜半翻身,便听它们“沙沙”作语。
离开乌鲁木齐前夜,再登红光雅居楼顶。博格达峰雪线在月光下泛出幽蓝,如岁月洗涤略褪色的哈达。轻声道别之际,深知地理已入文脉,呼吸已成节奏。
我把淮阳龙湖的四季也缝进同一只牛皮囊:春,母亲携我登宛丘祭风,土色苍褐,一捏即散,散后复聚,像被岁月反刍的谷核;夏,荷叶翻背,药味淡腥;秋,桂香沿水岸爬升,甜里藏苦;冬,冰裂“咚”一声,仿佛大地换齿。囊口束紧,它们与二十三种雪声并置,不分彼此,只待我写作淤塞时拆封——彼时天地替我张口,不必我再赘述。
《天山的雪》刊发前,编辑来信只一句:“你让天山在纸上长出耳朵。”而我深知,那些耳朵早在我援疆三年间的桦树皮卷里,就已悄悄张开。
钥匙二:气味让记忆先于语言醒来
写作心法:气味比文字更不讲理。它绕过理性,直抵杏仁核,于彼处点燃一簇幽蓝火焰。写作时,我常将“气味”当作第一把钥匙,先于情节、主题与结构,任它将门推开。
小时候,在河南老家淮阳,我惯于黎明沿蔡河小跑。秋深时,满觉陇桂香如一条暗河,沿凤凰台古桥石阶缝隙上涨。那香气非一味甜腻,它带着凌晨四点的清冽、露水坠地时的轻颤、花蕊深处几不可察的苦药味。我将这些折成薄纸片,塞入记忆口袋。日后写《花酿》,只需拈出一片,整个秋天便哗地一声在稿纸上铺开。
刊物对读:《散文》处理气味,如老茶客品干茶:轻轻一嗅,便知年份与山场。不纵容铺陈,而让气味成为一条暗线,于叙事松弛处悄然探头。
《五色土》让气味携胡同口的豆汁焦圈、太庙古柏的松脂味,一同扑人满面。
《花地》则敢让气味掀帘而出,甚至允其成为主角。如写岭南荔枝,作者以千字篇幅摹写荔壳在烈日下迸发的蜜甜,似要让读者鼻息永驻六月。
自我审视:《花酿》已被《散文》编辑部留用,拟近期刊发。文从母亲手植丹桂起笔,至小暑那日她于灶间蒸米、拌曲、封坛,墨中掺夜合花汁,于坛身书“花酿”二字。全文三千余字,分五嗅:初嗅“凌晨四点露坠花蕊的清苦”,再嗅“蒸汽冲开木盖时的幽甜”,三嗅“封坛三年后启封的苦后回甘”,四嗅“火车北上前夜母亲塞入行囊的涩暖”,五嗅“今夜北京出租屋里独酌时的冷香”。
二审删去一句:“那香气像母亲最后一次为我掖好被角。”批注曰:“让香气自己掖。”我照做。于是香气在纸上自已动了手,读至此,多下意识拢紧衣领,似真有一瓣桂落在颈窝。
那缕桂香并非孤证。母亲去后,我回淮阳老屋,墙角纺车木轮缺齿,摇动声如碎玉;人祖庙钟声三响,风卷沙扑灭油灯。我拢手护住残焰,光投颓壁,竟化母亲侧影:伏羲星图、神农粟穗、子建诗石、东坡柳痕、范公蓑衣……皆成棉线,织入我血脉经纬。此刻我才懂,所谓“气味地图”,不过是替母亲守口,让她的呼吸先于我的语言醒来。
钥匙三:声音让节奏先于意义发生
写作心法:声音是散文的潜台词。它先于意义,先于情感,如一只看不见的手,替读者将心脏调至某种频率。
写《风铃响处》时,曾深夜登北京鼓楼,录风掠铁马之“缺一拍”。回淮阳守灵那夜,又录龙湖冰裂的“咚”声。两段声音在剪辑软件中首尾衔接,严丝合缝如一声心跳。我将此声嵌入文章第三节《缺拍》,让它为母亲补全未竟的鼓点。
刊物对读:《散文》版式留白充裕,如予声音回旋长廊;允沉默成为另一种声音。
《五色土》则让胡同鸽哨、后海桨声、雪落凤凰台的“咚”响,共织北京晨昏。
《花地》不惜版面,将整页让与排比、重复、呼喊,似要让纸面共振。
自我审视:《风铃响处》刊于2025年8月26日《羊城晚报》“花地”头条,新华网客户端转载,当天33万读者浏览。全文分四折:风过鼓楼、银锭桥、后海、淮阳。每折末尾留三行空白,空白处印极浅风铃线稿,任读者自填耳畔声响。发表后一周,收四十七封来信,有人听见“母亲最后一次掖被角”的窸窣,有人听见“铜钥匙插入冻土”的闷响。声音于此完成二次分娩。
鼓楼缺拍、龙湖冰裂之外,我又录下第三种声响:淮阳柳湖夜祭,玄衣老妪肩荷雕花扁担,铜铃叮当,似星子碰碎薄冰;稚童摸“子孙窑”,指尖粗砺石纹与我童年拾粟之手重叠。我把这串鼓点裁成三小节,嵌进《风铃响处》空白页,读者掩卷时,听见的是母亲藏在石纹里的心跳——风从龙,龙角初升则春回,鼓声未绝,春便不凋。
钥匙四:语言如月色明暗、温度、留白
写作心法:语言是散文的肌肤,更是呼吸。好语言当如月色:不止照明,更渲染氛围、层叠心境。月色有明暗之交、冷暖之变,更有无言之处的丰饶——那便是留白。
修文时,我循“删减律”:先砍形容词,审只剩骨架的名词动词能否自立;再删副词,观剥离修饰后文章情绪与节奏是否更显遒劲。
刊物对读:《散文》用纸薄轻而韧,翻动时“沙啦”脆响,清冽如新竹踏雪。版心疏朗,字行留裕,似编辑深恐排满,惊扰文字沉思。
《五色土》用纸略带毛边,抚如老城墙灰砖,留得住指纹,亦留得住月光。
《花地》纸质厚重,色泽温润,抚之可感纸基肌理微凸,如山川暗藏掌下。彩插山水画非赘余,似为浓墨重彩的文字披缂丝罩衫,华美自成。
自我审视:《母亲与荷长相伴》(2025年8月24日《北京晚报》“五色土”文艺副刊),写于母亲离世后第一个冬至。初稿写至“钥匙插入坟前冻土”时,连用三“深”:深冬、深土、深念。编辑回信:“让钥匙自己往下走。”遂删尽“深”字,只留“钥匙插入冻土,深及三寸”。一字不余,却听见钥匙继续下沉,沉入所有读者心里。
冬至删“深”字那夜,我忽忆母亲携我立于宛丘圭表下,影指巽宫,角宿微芒。她说:“风从龙,龙角初升则春回。”言罢不再解释,只留月色在圭表上慢慢爬行,像一条不肯就范的河流。我把那道月痕留在稿纸边缘,未着一字,却替所有读者省下一声叹息。
钥匙五:文化不是标签,是呼吸
写作心法:时下散文多患“文化名词堆砌症”,似不引经据典便无厚度。然文化之于散文,不应是襟上徽章,而是流动血液的氧,是呼吸间自然带出的温度。
化用之道,非为掉书袋。写西湖,不必硬写“苏轼曾疏浚淤泥”,可写“船桨拨开水面,仿佛听见千年前‘欲把西湖比西子’于湖心咕噜冒泡”。让典故复活,与当下情境发生天人合一的反应。
刊物对读:《散文》处理文化,讲“化血入水,静水流深”。典故学问被彻底溶解,表面无波,深处暗涌。
《五色土》则让康熙通宝与豆汁焦圈同席,《三字经》与胡同叫卖共响。
《花地》敢“点火烹油”,让文化碰撞更显性、炽烈。岭南骑楼与《楚辞》香草并置,粤剧与南洋帆影交响,如一场文学化装舞会,色彩浓烈,情绪奔放。
自我审视:《风铃响处》中,未直接引用《古文观止》,只写母亲誊至“聊乘化以归尽”时,笔锋轻挑“尽”字末捺,似为我留半瓣未写完的花。读者却从此捺中读整部《归去来兮辞》。
淮阳旧渠底,母亲曾拈出一粒炭黑粟:“神农引泉溉田时,它就在此做梦。”我未在文中引神农一字,却让那粒粟在《母亲与荷长相伴》的湖水里悄悄发芽,长成七粒莲子。读者摸到莲心苦时,自会听见“先忧后乐”的暗涌——文化至此,只作呼吸,不作注脚。
钥匙六:修改是第三次创作
写作心法:许多人视修改为苦役,我则尊其为“第三次创作”。初稿是情感原矿;二稿理智介入,疏通逻辑;第三稿始,心脑深度融合,作品方获独立生命。
常用三法:一是朗读——除普通话,更用方言。吴侬软语检节奏,中原官话查逻辑;其次逆写——从尾到头拆解文章,审记忆链条是否坚固;再者冷置——完稿后锁入抽屉,候一场秋雨的时间,让情绪冷却,再辨铁锈。
刊物对读:《散文》编辑来信字迹清瘦:“气韵已足,然可再瘦三百字。”这“瘦”是减赘肉、显骨骼,求水一般的澄明。
《五色土》则说:“留一口京味儿,别太满。”
《花地》回信:“情致正浓,何不再泼墨三篇?”这“肥”是添柴火、让燃烧更彻底,求油一般的丰沛。
自我审视:《天山的雪》初稿写尽二十三种雪声。冷置两月后,删去六种,只留“雪落松针”“雪崩前”“雪水渗土”“雪融阳光”四声,恰对应“起承转合”。刊后,有新疆读者来信:“我听见了自己的童年。”
冷置《天山的雪》两月,我返淮阳撮故园温土覆稿,指尖触到半片黑陶星盘,银星镶角亢二宿。盘底“坎”卦刻痕仍留姚燧指尖温度。我把星盘翻个面,让雪声与卦象互为倒影——删去的十九种雪响,终在陶片暗纹里重新落座,如一场无声的流星雨,完成第三次创作。
钥匙七:把“我”放进字缝里
写作心法:散文核心是“我”,但文学的“我”需淬炼、打磨、伪装,既保个人印记,又能照亮他人隐秘角落。
最高明的“我”,是藏起来的“我”。写离别,不必嚎啕,可写十六岁那年攥在手里、被汗水浸得字迹模糊却终未送出的信;写重逢,不必直抒,可写昨夜梦里才见的侧脸,醒来指尖犹存触感;写死亡,不必渲染悲恸,可写亲手折就、放入河中转眼被漩涡吞没的莲花灯。
刊物对读:《散文》处理“我”内敛克制。卷首语常如“未寄出的信”,寥寥三百字,淡如清茗,却以一句极轻感慨击中共鸣。
《五色土》让“我”立于胡同口,手中攥一把铜钥匙,齿缝间还沾太昊陵的香灰。
《花地》则让“我”纵情高歌。千余字的字里行间,含万字长梦,记忆、幻想、呐喊交织,求非沉默共鸣,而是直接感染力——要让清晨四点的读者掩卷仍热泪盈眶。
自我审视:《风铃响处》里,将自已藏入一只未撑开的油纸伞,伞面“无远弗届”四字,墨中掺夜合花汁,甜意极轻,却足以撑住整座北京城的初秋。
《母亲与荷长相伴》里,则将自已藏入七粒莲子,让它们在冻土深处悄悄发芽,长成母亲与我之间最长的藕丝。
而《花酿》最末,写:“熄灯时,芦管竟透出一点微绿,似母亲当年夹入书中的最后一瓣桂。”那一点微绿,是我,也是母亲,更是所有读者心里不肯熄灭的灯。那灯芯原是母亲折蓍草插我衣襟时留下的哨音。多年后,童女捧麦穗踏浪而来,将蓍草灯芯递我,火舌舔着草节,发出极轻的爆裂,像替母亲回答我未竟的告别。我把它搁在字缝最深处,只露一星,照见我们终将重逢的春灯。
文字把根须一寸寸扎进人间烟火
日头渐高,陶然亭湖面的波光粼粼,在光的温度与水的涌动下渐次化开,被湖水吸收,终至无痕。水面复归平静,如一面阅历深厚的旧铜镜,映照天光云影,亦涵纳方才的绚烂。
写作之道,又何尝不是如此?水性沉静,让我们潜入生命骨血深处,探寻存在本质;油性热烈,让我们奔向历史山河旷野,张扬生命活力;而五色之土,则让我们把根须一寸寸扎进人间烟火,文化的力量风雷激荡、春风化雨。
在这条奔流不息的文化河流中,你书写它,它亦反哺你、塑造你。最终,你写就了文章,文章也写就了你。
作者为光明日报《博览群书》杂志主编、文化学者、散文家
扫码在手机上查看